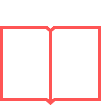淌鱼
{{sourceReset(detailData.source)}}{{dynamicData.sub_info.subject_name}} 紫牛新闻
{{wholeTimeFilter(detailData.happen_time)}} {{numFilter(detailData.review_count)}}次阅读
{{numFilter(detailData.review_count)}}次阅读
据气象台预报:近几天有雨,雨量中等。谁知那天夜里就下起了倾盆大雨,伴着电闪雷鸣,好像老天爷把天河的水都倒下来了,整整下了一天一夜,沟满河平,整个街道都被淹了。村里的鱼塘无一幸免,连马路上都有鱼逆流而上,激起层层浪花。大人小孩拿着小网,追逐鱼头,欢声笑语,渐行渐远……
眼前这一幕又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。那天是六月六节气。从夜里开始下起瓢泼大雨,到天亮还没停。我家住的面朝西的两间草屋,雨水从石头缝流进屋里,弟弟妹妹们吓得依偎在母亲的怀里,直打哆嗦。母亲紧搂着他们自言自语地说:“六月六下雨,反晒龙衣四十天,今年荒年是肯定的。”灶后的一点草也被雨水浸湿了,没有草烧饭,和全村人家一样,都这么忍着饿。大约十点左右,雨逐渐停止,大家才开门。哎呀,我的天哪!四周一片汪洋,村庄就像汪洋中的一个孤岛,我们跑到菜园子水里摘点西红柿、茄子、面瓜充饥,有的人在菜园子里都抓到了鱼。野兔在水中挣扎,终因无处歇脚而被淹死,被人们捡回家成了盘中餐。小孩子被大人管在屋里不准出门——处处是水,太危险!
开举大伯是生产队长,雨稍微小些,就用喇叭喊所有男劳力,披着塑料纸或蓑衣等防雨工具,扛着锹和铁铲,冒雨挖沟,疏通河道,抗洪排涝。妇女们忙着掏草堆里的干草做饭。当时月翻河刚挑不久,因为太浅,被水冲沙填也只有一个河影子了,但仍然是我村泄洪排涝的主河道。四面八方的水被引向月翻河,汇成一股混浊的激流,摧枯拉朽的向北方急泻而下,穿过缪庄涵洞时,因洞小水大而受阻,形成巨大的浪头,扑向洞壁,又反弹回来,就像钱塘江大潮一样,聚成二次大浪撞向涵洞,发出吓人的轰鸣声。河床上淤积的泥沙,被激流冲刷殆尽,河中间漩成很宽很深的大沟,恢复了河的模样。大田里每块地都有人守着:凡是有不通畅之处,立即挑开泥土,把水排清。
经过五、六个小时的排水,农田才露出本来面目。只有沟里还有不少的水,伴着鱼儿在流淌、嬉戏。这个时候是淌鱼的最佳时机。我和堂弟昌兵四处寻找能淌鱼的地点。在缪庄门前大塘南边,紧挨着塘有一条沟,沟底已经被生产队派人又挖了两锹宽,大塘和沟之间已切开排水,肯定有鱼!我们决定就在这里淌!但是抗洪排涝期间不能明目张胆的打堰拦水淌鱼,如被队长发现,除了没收淌鱼工具外,还要被扣工分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!
我们回去吃了早晚饭(一天就这么一顿),我和昌兵抬着小凉床(用木棍打的框子,按上四条腿,网上用茅草搓成的绳,铺上芦席,夏天乘凉,因此叫凉床),带上窝篓、筛子、铁锹、小鱼篮、木板、马灯(带玻璃罩子的防风灯),悄悄的到缪庄沟边(有点像《地道战》里面的鬼子进村),天还没有黑,我挖了一堆方垡块子(昌兵力气小,挖不动),然后下到沟里,叫昌兵把土搬给我打堰,搬不动就在地上把方垡翻给我,反正有扒根草连着,方垡也不会碎。我从沟底一层一层往上叠,一条底宽上窄的堰坝打好之后,先把水潏住,等到水位上涨到二十公分后,再把堰扒开一个六十公分宽,十公分深的口子,放上木板踩平,把口子两边的坝壁用油泥揣实,防止被水流冲垮。把筛子放到木板下游的底下固定垫实,周围用芦苇扎成柴把子拦着,防止鱼淌进筛子后撅出去,同时在木板前头插一根带叶的芦苇,引诱鱼儿往下游。兄弟俩足足花了近一个小时,才一切就绪,洗洗手脚,睡到凉床上,就等坐收渔利了,不一会昌兵就睡着了。
天渐渐地黑下来,我把马灯点着,为了省油,把灯芯捻到最小,就像萤火虫的尾巴,一闪一闪的,还真的招来不少萤火虫,上下飞舞。天黑了,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风呼呼的刮,刮得树叶和芦苇“唰、唰”作响,树上的知了也因喝足了雨水不再振鸣。远处响着闷雷,不时有闪电在空中像银蛇一样划来绕去,透过电光,看到天上乌云翻滚,随着风,堆起团团云浪。不远处有几座老坟,上面长满了草和杂树,隐隐就像几个大草垛。芦苇丛里不时传来一两声野猫亦或是夜鸟的嚎叫,很是瘆人。有两只赖蛤蟆不知疲倦地“嗯-啊-嗯-啊-”的一唱一和,其余剩下就是寂静。我有点害怕:怕有大蛇,怕有鬼怪,怕……
突然,远处传来“踏啦踏啦”的声响,而且越来越近,我在床上透过一丝亮光望去——有一个黑影,头如笆斗,身体粗大而带毛,就像故事里讲的“夜游神”一般,吓得我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,连忙推醒昌兵,把灯光捻大,手握铁锹,颤抖地大声喝道:“哪个?”对方也被我突如其来的断喝吓了一跳:“你是哪个?”听到对方说话了,知道是人,悬着的心才放下来,走近一看,原来是三队的李大爹(化名),戴着斗篷,穿着蓑衣(蓑衣有好多种:有蒲叶编织的,有高粱叶编织的,有莞草编织的,有茅草编织的等等),背着柳簸箕,拎着铁锹和鱼篓子,就和传说中的“毛人水怪”差不多,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说:“李大爹,你吓死我们了!”他放下身上的东西,兴师问罪地说:“你们两个小鬼,胆子真大,竟敢在我们三队的沟里淌鱼,我告诉队长收了你们的东西!”我心想这老头说话真是欺人,“五十步笑百步”,分明是想霸占我们打好的堰淌鱼,反而要恶人先告状,按照我们农村话叫“烧不熟”。于是我说:“你别废话,要淌鱼你就在我们的堰上按筐一起淌,不淌你就走,告诉队长我也不怕,‘贵太爷’和我们是亲戚(缪佃贵是队长,按辈分我们叫贵太爷)。”听到这话,他心满意足,不费一点力气,在我们打的堰上淌起鱼来了。我想让着他吧,有个大人仗仗胆也好,省得我们害怕。他把淌鱼工具弄好后,把蓑衣放在地上,半铺半盖,不一会,我们就放心地进入了梦乡。
不知什么时候,我被水声惊醒。抬头一看,是李老头下水到柳簸箕里拿鱼,我也起来到筛子里拿鱼,结果连一个小鱼都没有,李老头没来时,我每次总能拿到“小刀壳子”(鲫鱼)、撅嘴餐子(白条)、“肉罗汉”什么的,我知道已经被李老头抢先拿了,但我没有说破,从此监视他的一举一动,只要他起身拿鱼我就盯着,他把手伸向筛子时,我就咳嗽警告他,几次搞得他很尴尬。
在我迷迷糊糊、似睡非睡时,听到木板上的水流声不太正常,断断续续,似乎上游有什么东西挡住水流,我分析是有大鱼到堰前见水浅,游不过去又回头了,鱼的身体和尾巴的摆动挡住了水流,发出“哗哗”的声音,看来到五更天了,鱼开始活动了。我的困意顿消,准备逮大鱼!果不其然,那条大鱼经过几次试探之后,一跃而起,猛地一道白光,从堰的上游飞过筛子,“澎”的一声,落到下游的沟里,我立即起身,冲到离筛子五、六米的沟里,蹲下身子挡住鱼的去路,李老头抢到我的前面,我声东击西说:“还在前面!”李老头和昌兵一路向西摸去,我掉头向堰坝前摸,只走了两步,就探到大鱼的尾巴了,我立刻蹲在水里,扩大拦鱼面积,堵住鱼的退路,慢慢把鱼挤到了筛子底下,使它无路可逃。可是鱼太大、太滑,怎么也降服不了,只好双膝跪在鱼身上,双手按住鱼头,使出浑身力气,才把鱼放平。幸亏沟只有两锹宽,鱼在水里没有回旋余地,否则还真按不住它。鱼在水里威力全靠尾巴,鱼尾巴就像船的舵一样,船没有舵自然不能行驶了。我腾出一只手,用力掰开鱼鳃抠进去,另一只手从鱼的口中伸入,终于把这条大鲤鱼捉住了,连拖带拽把鱼拉上岸,放在窝篓里,鱼的头和尾巴都露在篓子外边,我把小凉床搬过来压在窝篓上,人一屁股坐在床上直喘粗气,太费劲了,感到手臂酸酸的,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李老头和昌兵听说我逮到了大鱼,赶过来要看,我对昌兵说:“兄弟,现在黑天倒地的不能看,等天亮再看。”于是兄弟俩一起坐在床上“镇守”,李老头多次要看,都被我们拒绝。
打此时起,我们兄弟俩不敢离开小床,眼睁睁看着李老头多次把我们筛子里的鱼捞走。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。东方露出鱼肚白,我捻熄了马灯,兄弟俩收拾东西准备回家,李老头过来说:“大连生(昌兵的乳名),我们三人逮的鱼,怎么能让殷小重(我的乳名,我家有老太太,取重孙子之意)一个人拿走呢?应该平分!”昌兵说:“关你什么事?”李老头看挑不起事,亲自上阵想动手抢鱼,我端起铁锹对准他说:“你已经拿了我们好几斤鱼,还不知足,如果还想以大欺小抢我们这条大鱼,别怪我铲你!”他看着雪亮的锹口,胆怯了,边退边说:“这小子真愣!”眼巴巴看着我和昌兵把东西收拾好,因路上还有几道沟要走,为了防止万一,我把小褂子脱下来,用衣袖子把鱼鳃穿过来栓在床框上回家了。
一夜的大风,把天上的云都吹得差不多了,余下的云被朝阳映得红彤彤,金灿灿,银闪闪的。大地被射得流光溢彩,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,空气一片清新,令人心旷神怡。
我和昌兵抬着小床,床上卡着窝篓,就像在战场上得胜凯旋的士兵。刚到庄后的圩门嘴,昌兵就喊:“快来看呐,大哥逮到大鱼了!”庄上的人听到喊声都围了过来,边看边说:“乖乖,只有缪庄河里有这么大的鱼,啧!啧!不简单!怎么逮的?”我非常高兴、手舞足蹈地向他们描述了逮鱼经过……回家用秤称了一下——好家伙,十二斤多呢!我对昌兵说:“兄弟,鱼篮里几斤小一点鱼你先拿回家给二妈(昌兵母亲)煮,大鱼中午我妈煮好了哥送到你家。”昌兵高兴地回去了。
由于是夏天,天气炎热,不及时处理鱼会坏掉,我母亲用刀把鱼胣了。那鱼鳞有“袁大头”(银元)那么大,鱼肝、鱼油、鱼肚、鱼籽扒了一盆。中午,我母亲把鱼剁成“东坡肉”大小的块子(大约一寸五见方),八张锅煮了满满一锅,放了辣椒、芫荽、大酱、盐等,那汤鲜珍珍,辣抽抽的,老远闻着就扑鼻香。全庄十来户人家,每家送一碗。当然,昌兵家要比别人家的份量多。庄邻都夸我母亲的厨艺好,夸我逮的鱼大——好吃!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,就是过年也不一定能吃到如此美味,我也知道有恭维的成分在内,吃好说好嘛!
秋学期开学后,我到黄圩读初中了。打那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淌鱼了。现在一遇到下大雨,就想起少年时淌鱼的经历,想起那次逮大鲤鱼的经过——那是我一生中徒手逮到的最大的鱼了,也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一顿鱼,所以回味无穷,久久不能忘怀……
几十年后,想起儿时的无知不懂事,对李大爹的不恭,常感歉意,但他老人家已经作古仙逝,只能对着苍天说声“对不起”了。这件事时时警醒自己,要孝敬长辈,尊重同辈,关爱晚辈,教育后代——人心向善……
更多内容请打开紫牛新闻, 或点击链接